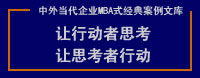断裂货代链谁扣押了“义乌货”?
加威的故事
当加威(Javid)怯生生地出现在宁波海事法院,甚至“未语泪先流”时,法官顾雅琴无法不表示她的同情:“一个大男人,如果不是到了这个地步,不至于如此。”
这个巴基斯坦男人在“中国小商品之都”经营着他的生意——采购小商品并托运回自己的国家。最近,他的一份提单(从巴基斯坦港口提取货物的凭证)被宁波的一家货运代理公司扣押了,原因是这家公司一直没有收到义乌一家上级代理公司的运费。
类似的“加威案”正在宁波、义乌频繁上演。2006年全年,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的“海事强制令案件”达80多起;2007年后,此类案件呈现明显增多趋势,自去年12月下旬至2007年2月上旬的仅40多天内,宁波海事法院合计受理“海事强制令案件”近20起。前后近100起案件涉及外商60家,涉及一级货代企业30多家,涉案贸易总金额达数千万元,涉案运费总金额超过千万元。
去年,加威受委托采购了一批陶器、生活用具、工艺品等小商品。为了运输这批货物,他一直通过深圳快顺通国际货代义乌分公司托运货物,再由这家公司委托给上海帝运国际货代宁波分公司具体承运,货物在宁波装船出海。“每个集装箱,我付给义乌的代理公司1800美元或者1900美元,高的时候2000美元或者2100美元,然后,他们会帮我解决从装箱开始的所有问题。”
在此之前,这种操作方式一直运作得非常顺利,但是没想到这批货出了意外。原本,在从义乌发货之后的一个星期内,提单就应该到达巴基斯坦的收货方手中,但三个星期过去了,这箱货的提单仍然不见踪影。
加威开始满义乌找寻这家一度合作良好的货代公司,但是那张曾经和善的面孔已经“人间蒸发”。
走投无路的加威正式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申请“海事强制令”,要求负责承运的帝运宁波分公司必须交出提单,加威向法院出示了他已经向快顺通支付了有关运费的证明。
事情最终有了一个令加威满意的结果。由宁波海事法院出面,在加威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之后,帝运宁波分公司交还了这份提单。一个月后,加威又从宁波海事法院取回了他的押金。
不过,加威至今仍不十分不清楚,帝运宁波分公司为什么要扣押他的提单,他只听说“义乌的公司好像欠了宁波公司的钱”,“但我的钱都已经付清了。”加威说。在发生“提单扣押”事件之前,加威从来没有、也不必和帝运宁波分公司接触,虽然,帝运才是加威的货物的“真正承运人”。
加威是幸运的,他的经验也正在适用于其它“被货代公司扣押提单”的货主:“申请海事强制令”,强行拿回提单。“海事强制令”的出发点在于,在解决争端之前,避免“被请求方”(此处指“帝运宁波分公司”)对货主(此处指“加威”)的合法权益“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”。
“加威案”涉及在义乌采购的国外货主、义乌当地的中间货代公司和宁波的一级国际货代公司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?
委屈的“被告”
交还提单后,那些一级货代公司们拿回运费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。
这些公司之所以扣押提单,是因为那些从货主那里揽货、然后再委托他们运输的上级货代公司们,已经拖欠了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运费。而且,这些中间货代,要么人间蒸发了,要么就是“你偶尔能够打通他的电话,他也承认有这笔账,但就是没钱还”。
杭州越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最近被请求执行“海事强制令”的一家一级货代公司,起因是越华扣押了始自一家义乌中间货代的16张提单。越华的一位人士表示,“这个货代已经拖欠了我们190万的运费”,而在16张提单被执行海事强制令后,越华“希望公安介入调查”,以追回运费。
据称,同样是这家义乌公司,还拖欠着上海某一级货代公司140万的运费。
厦门大顺大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董翼介绍:“在宁波、上海,这种情况很普遍,因为义乌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气,好多年了。”在最近的案件中,该公司扣押的提单同样来自义乌,被拖欠的运费为10多万元。
在成熟的货代业者看来,一些中间货代骗取运费的手法并不高明。董翼说,“货代做久了,这些手法大家也都清楚了”,“但还是会受骗”。
对于一级货代来说,与中间货代打交道最安全的方式是“付款买单”,“中间货代把钱给我,我把提单给他”。而骗案大多是从这种安全交易开始的,“他先跟你做两个月,付钱很爽快,而且,他的量会慢慢变大,你的利润看起来也是蛮好的”,“接下去他会跟你说,要么我们月结”。所谓“月结”,即由原来的“付款买单”变成“提单照样给,但3月的运费到4月10日给你”。
于是,漏洞出现了,因为“3月初到4月10日之前,中间货代手上会积累一笔运费”。“义乌的货主都是看到提单就付钱的”,“货主那边的钱他已经收了,一级货代的钱他还没付”。
在几次“月结”之后,这些中间货代的出货量会越来越大,它们甚至“不惜以低于运费的价格到义乌揽货”,“船公司报价1000美金,他报800”。
之后,它们将作出最后一击。“到最后一两个月时,比如,他8月给你出了很多货,9月10日,跟你打个招呼,说他周转有点困难,结款要拖几天,可能一直拖到9月底。这时候,他手上已经积累了两个月的运费了,并且金额非常非常大,然后,他就会逃之夭夭。”“几十万美金是很正常的,有时候甚至更多。”董翼说。
而一旦这种情形出现,货代链便告断裂。对于一级货代公司来说,“没有收到运费,我肯定要扣押提单。”而对于无法凭提单收货的货主来说,“申请海事强制令”便成为当然的选择。
脆弱的货代链
这些倍感委屈的“一级货代”公司们,都经过严格的资质认证,注册资金在500万以上,有成熟的运营经验。它们一般设立在上海、宁波等港口城市,或者在当地派驻机构。它们是整个货代链条上连接船公司的最后一环。
而所谓的“中间货代”,实际上并不具备真正的货代资质。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胡建新介绍说,“这些公司注册资金很小,可能只有10万、20万”,“它们做货运代理,可能也做外贸代理,但只是做这块业务,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代公司。”
货代运作的一般流程是:货主把货配给中间货代,中间货代把货配给一级货代,一级货代配给船公司;然后,一级货代从船公司拿到提单,交给中间货代,中间货代凭提单向货主收钱。其中,“中间货代”可能是一层,也可能是多层。
近期近20起案件,货物的来源基本都是义乌,胡建新总结:“这与义乌当地的操作习惯密切相关。”这些“习惯”包括:“出口多,外商多,代理多,现金交易多”。
在以“小商品”和“外贸”著称的义乌地区,外贸出口有它的独特之处。“虽然是外贸,但它是内贸形式的外贸。就是说,国外的客商直接到义乌市场订购,而出口时,因为我国外贸体制的原因,它必须要挂一个出口单位才能出去。”
对加威们来说,本地代理因此必不可少,不管是采购、外贸、还是货运,但代理的质量却并不能得到保证。“许多外商既不看营业执照,也不审核注册资金。甚至,有人冒充其它公司的业务员,拿一张名片就可以做生意了”。而且,义乌当地的小货代公司有的也不直接与宁波的一级货代发生关系,中间还有多手的代理,多层的环节。
这就为那些并不具备资质的“货代”提供了一个温床。事实证明,那些之后导致货代链断裂的中间货代,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,或者把资金挪作它用了,比如“炒炒房子,导致银根出现问题”,有些则是完全的“骗案”。“骗案”中的中间货代公司,往往“注册资金少”,其法定代表人也常常是一个“找不到的外地人”;胡建新说:“就算你找到这个公司,也拿不到钱。”
而义乌地区对现金交易的偏好,则是另一个便利条件。一方面,这为那些意图不轨的中间货代从货主手中圈钱提供了方便,另一方面,一些外商“交了钱,最后连证据都拿不出来”。
这些义乌“习惯”,最终孕育了一条“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宁波港”,“从外商货主到一级货代”,“从简单到复杂”的层层叠叠的货代链。但当分居两端、素未谋面的“货主”和“一级货代”相聚时,地点却是在宁波海事法院,他们之间最初的牵线人却早已消失不见。
“市场是你们自己做的,风险你们要自己承担。”这是宁波海事法院的态度,现实的建议是:“人家几十个集装箱一起过来时,最好几家一起做,就算亏了,也可以分摊风险。要注意交易安全,特别是义乌货”。